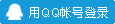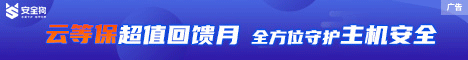「如今,在旅游行業重塑一個全新UGC的機會已經過去了」。螞蜂窩旅游研究中心的馮饒對我說。 淘在路上的破產,讓包括螞蜂窩在內的許多公司都心生感慨。 而已到了不惑之年的蟬游記創始人郭子威,近來也在為自己的創業項目在VC間奔走。看著競品落到如此田地,郭子威(純銀)在「簡書」的文章頗有兔死狐悲的感覺。 「淘在路上宣布倒閉,意味著從2011年到2016年,5年內新成立的to C端的旅行創業團隊全軍覆沒,幾百個團隊,幾億美金投資,全部化為烏有。」在路上、面包旅行、蟬游記這三家昔日在移動互聯網高增長的土壤中孕育出的移動端游記創業公司,都曾被寄予厚望。但在探索商業化轉型的過程中,紛紛折戟。 旅游市場的創業環境在寒流沖擊下,愈加萎靡。除了窮游、螞蜂窩,很多人都在懷疑,移動時代旅行市場的前景。但巨頭們卻開始重新審視內容社區的價值。 「我們要做的是用內容搶占用戶的時間」,阿里旅行新媒體總監劉春林興奮的向我介紹著他們做的社區與旅行頭條。 在已經尸橫遍野的旅游圈,內容社區又被重新撿起,旅游市場會不會借此有了絕地反擊的可能? 一 「如果我還沒有離場,我還想再打一場,重點不是如何反省個性缺點,而是如何找到并鑿開市場暗流。」雖然在微博上,純銀依舊嬉笑怒罵,最近卻多了些感慨。 想當初,在路上、面包旅行、蟬游記,作為移動攻略社區的代表,在移動互聯網高增長的紅利期,倍受追捧。 造化弄人,隨著資本寒冬的蔓延,沒有哪家公司能駕著七彩祥云成為顛覆攜程的蓋世英雄,人們等到的只有一個個被資本拋棄或是自我拋棄的故事。 蟬游記是三家中最先倒下的那一個。「雖然它還在維護,也將一直維護下去,但已經1年沒投錢進去推廣了,日活自然下滑,自然衰竭是遲早的事。」而這個結果,純銀在2014年底就知道了。 巧的是,與淘在路上一樣,蟬游記的敗亡也是源于融資失敗。「一次融資失敗,四年全盤皆輸」.「2013年,我的A輪融資完敗,之后只能算是茍活下來」。在純銀看來,2013年那次的融資失敗,打亂了蟬游記的節奏,連續錯過3個絕好的時間窗口。 做產品出身的純銀與當時創投界的主流觀點,格格不入。 拿到天使輪后,在初期組隊只有6個人,蟬游記是一個典型的產品基因壓倒運營基因的創業團隊。而當時的VC卻更看重「強運營」團隊,「強運營可以快速補產品,強產品很難快速補運營」是很多投資人的觀點,「運營才能建立壁壘,拿到融資以后請幾個好一點的產品經理,產品很容易拉起來。」 因為運營不夠強,在2013年談A輪的時候,由于蟬游記單iOS端的日活1萬出頭,數據在幾家競品里邊是最少的,鮮有VC愿意出手。 「VC的邏輯可能也很簡單:一眼看過去都是游記,那就投數據最好看的。」純銀自己的復盤,言語中有著不少無奈。「融資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講的故事不吸引人。」 純銀為VC準備的故事是「游記數據自動結構化→結構化旅行攻略→分發旅行商品」,而競品的故事是「游記→社區→商品&旅行社」。 「我完全能理解2013年VC不投蟬小隊,當時是移動互聯網高增長的紅利期,新用戶見識少,就算產品品質不好,使出各種運營手段也能大量獲取用戶,所以的確是運營比產品更重要,社區故事也比攻略故事更動聽。」 2013年的社區概念特別火,但純銀卻堅持認為低頻無社區,打死不走社區路;VC在看到數據增長之前對攻略的概念卻不感冒。而讓純銀最尷尬的是,在許多VC眼里,他只是個產品經理,卻一直不看好他做創始人。 「當時談了35家VC,只有攜程一家在年底愿意投我們,但要求控股。」這次,純銀沒有拗過大腿,與攜程簽了城下之盟。攜程1200萬的A輪投資,并沒有為蟬游記帶來蛻變,反而如雞肋一般,陷入了自生自滅的境地。 事實證明,純銀自己的推斷是起碼沒有錯。 與另外兩家直接競品5-6億的ABC輪投資相比,蟬游記的融資額度少的可憐,但最終的結果都差不多。 「這個市場唯一不大不小的機遇,是2012-2013年的輕攻略,被老字號的螞蜂窩和窮游抓住了」,純銀自己也后悔當初在2014年攻略市場的時間窗口關閉之時,才帶著蟬游記殺入。而陳偉也因為忽視了淘在路上社區的價值,直接向平臺邁進,與OTA正面廝殺。 最后,蟬游記2015年之后處于凍結狀態,淘在路上倒閉,面包近期也放棄了旅行業務線。「移動互聯網的旅行市場是一個貧礦」。這個市場在5年內所謂的市場機遇,看起來的確更像是水中月鏡中花。 社區的商業化,看上去依舊是個難題。而就在之前,旅游社區還是被視為是帶上金箍的至尊寶,激起了無數旅人的英雄夢。 二 天生驕傲的窮游與螞蜂窩,是無數旅行者心中的兩面旗幟。 「窮游是十年前基于創始人的個人興趣創立的,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行為。」2004年,還在德國留學的肖異,出于分享與互助的意愿,開設了一個旅游論壇「窮游歐洲」。這是一個以留學生為核心的互助社區,最開始這個論壇的用戶全是在歐洲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把自己出去旅行的一些信息和一些時效性的東西分享出來。 PC時代的旅游市場,很多從業者是靠著目的地的信息不對稱賺錢的,而旅游社區的出現就是為了打破信息的壁壘。 「窮游是從歐洲開始的,起初推薦大量關于如何在歐洲玩得更加聰明的帖子,幫助用戶不花冤枉錢。至始至終,我們根本性的東西還是輔助用戶做好決策,告訴用戶如何在國外花更少的錢,玩得更有意思。」 當肖異一個人在德國精心維護著自己的窮游網時,國內也有兩個互聯網人,有了類似的想法。 陳罡與呂剛,是兩個原本沒有交集的人。陳罡的外表是個終日坐在顯示屏前的典型IT男,而留著長發的呂剛卻有著朋克范,喜歡騎哈雷。這兩個人由于工作的原因進了搜狐,卻因為共同的愛好從普通同事變成了基友。2006年,在兩人基情的孕育下,螞蜂窩也誕生了。 PC時代的窮游與螞蜂窩,一個專注境外,一個起于境內,一個注重交流,一個注重分享。在商旅時代,這兩個網站對于許多旅行愛好者來說就是兩股清流。 那個時候的窮游與螞蜂窩也相對純粹,也為兩家網站沉淀了一大批忠實的種子用戶。 窮游總裁蔡景暉介紹,窮游從04年到11年一直在積累,到11年窮游網站大發展的時候,他們發現以前的積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認為雖然當時的模式看上去發展的特別慢,但這種積淀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厚積薄發,前期你需要非常非常慢的一個積累,不停的篩,把最好的用戶留下來,把最好的氣氛保持住,然后把最精準的訊息最好的留下來,這樣才能把這個網站最精華的東西留下來」。 直至今日,很多旅游企業更多解決的是「買賣」的問題,但年輕用戶的另外一些需求,如旅游深度內容體驗、基于共同愛好的社群互動、目的地旅行社交等方面的供給卻無法與用戶需求匹配。 如何個性化的出游,成了很多人的核心訴求。窮游、螞蜂窩的出現,正好又適應了這樣的需求。 三 「我們在門戶信息的形態上開創了垂直社區這種新的產品形態并運營了10年。垂直社區比起來上一代門戶社區里面有本質上的革命和創興,絕非僅僅是做了一個子集」。窮游COO韓哲認為,他們做的事的意義在于信息民主化的創新,同時也有情感傳遞和連接方法的創新。「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價值跳躍」。 2011年,是消費升級的開端,也正是移動互聯網興起的年份,也是社區商業化的拐點。螞蜂窩和窮游在相繼拿到融資后,也分別在2011、2012年初推出了自己的移動端App。而這時,市場中以在路上、面包旅行、蟬游記為代表,一大批移動端的游記攻略創業公司出現了。 不過,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消費升級后,「分享游記」的門檻正在變得越來越低,旅游這件事也漸漸大眾化,用戶的需求也愈加多樣化。 傳統的UGC社區是用戶產生內容,然后平臺進行篩選推薦整合,進而形成結構化數據,如攻略、游記的手冊等。但由于信息太過碎片化,很多用戶不得不自己從海量的內容中提取有效信息,體驗相對糟糕。 「用戶的變化越來越快,原來值得驕傲的產品,新生代的年輕人們未必喜歡,產品得跑的比趨勢快,跑的快就容易犯錯誤,窮游本身的產品其實是讓大家不工作慢下來看看世界的,有點矛盾。」韓哲承認移動是個換軌道的事情,很多創業公司做的艱難,而窮游也在努力中。 在社區的商業化過程中,窮游、螞蜂窩的優勢在于,經過多年的旅游攻略和UGC(用戶內容原創)內容的沉淀,已經聚集了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注冊用戶,而且成本極低,但距離交易環節卻很遙遠。 一個殘酷的用戶習慣是,很多用戶在相關網站上研究了很久的攻略后,還是去攜程、阿里旅行這樣的App上預訂產品。 如何找到內容與交易的契合點,成了關鍵。其實兩家公司都先后在內容之外陸續做起了機票、酒店等產品的零售,但現在看來,兩家公司的道路截然相反。 窮游這家運營了十多年的純線上社區,走到了線下。在標品市場里與OTA硬碰硬,顯然不是窮游擅長的,他們選擇在「當地玩樂」領域探險,以清邁為試點,陸續在幾個境外的目的地建立了Q—Home。 韓哲說,清邁的Q-Home不僅擔當著地接社責任,它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對供應鏈的掌控。他們在目的地采取直采、買斷的方式,「批發」目的地的特色旅游產品,縮短了供應鏈。除了在自己的平臺售賣外,窮游還將這些產品分銷出去,利潤率比國內 OTA 行業的平均利潤率高幾倍。 而螞蜂窩選擇了「攻略社區——大數據公司——自由行服務平臺」的道路。陳罡說,螞蜂窩起家之初依靠攻略搭建起來的社區,僅僅是「螞蜂窩的外表」,他認為螞蜂窩最核心的競爭力在于數據。 「螞蜂窩前幾年就是在做攻略,搭社區,如何用攻略吸引更多的流量。之后是做大數據,要把用戶在螞蜂窩的瀏覽全部大數據統計,以此來找到用戶需求和商業的結合點。這兩年,螞蜂窩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交易。在流量和大數據搭建好的基礎上,如何把它的商業價值發揮到最大。」 歷經了資本寒冬的洗禮,旅游社區的格局又回到了往昔。窮游從一個 UGC 的分享平臺,變成了一個重資產的公司,而螞蜂窩則像極了自由行領域的天貓。 不過,內容社區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因為,有人重新入場了。 四 當全世界的內容社區都在向電商轉型時,全世界的電商卻一窩蜂的做起了內容社區。 秒殺、滿減、買贈、折扣、任選等等各種方式的低價刺激,這種方式在電商發展初期非常管用,但這樣的打法在最近越來越不合時宜。 立志要做百年公司的阿里猛然間發現,雖然手機淘寶有著日均1億的日活,但流量已經見頂,低價的玩法顯得愈加傳統,貨架式的銷售走了下坡路,自己居然變成了「落后勢力」的代表。 「電商+內容」成了阿里新的營銷手段。隨著內容形式的多樣化,包括圖文、視頻在內的很多優質內容都可以用來賣東西。淘寶為此做了微淘、社區,力推淘寶頭條;京東做了發現;聚美優品也在首頁嵌入了一個完整的社區。 其實「內容電商」與一般的電商模式無異,最大的區別其實是在于垂直化,并通過優質內容幫助用戶決策,從而實現購買。而內容與旅游有著天然的默契,阿里的這套理論不但被應用到阿里旅行的實踐中,也與自由行領域玩家的觀點不謀而合。 「2016年旅游圈倒下的公司,幾乎都是堅守著舊有的電商思路和貨架模式」。馮饒解釋說,「傳統OTA舊有的電商模式已經無法滿足自由行時代的到來」。按照傳統電商思路來做自由行服務,貨架成為了唯一的銷售手段,致使「大路貨賣得好」、「從業者無利潤」成為了從業者共同的痛點。 「于是在傳統OTA上,我們看到,產品過于單一集中,而個性化產品又很難賣出去。大家仿佛和跟團游時代一樣,陷入了同樣單一產品的價格戰——但對于自由行用戶來講,這完全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馮饒認為,價格敏感本身就是用戶無法做出有效消費決策最明顯的行為——因為沒有信息幫助他們做出判斷,而只是價格成為了首要的判斷標準。「這其實是違背互聯網思維的。這也是為什么作為在線電商巨頭的阿里,會花重金去重新打造內容」。 在阿里旅行App的發現頁面,涵蓋了旅游資訊、圖文攻略、視頻、VR、直播等一系列內容,還增加了很多社交上的功能。 劉春林坦言,與淘寶的實物電商不同,旅游產品的體驗無法提前預知,決策時間也很漫長。那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內容對用戶產生強刺激,幫助商家提升內容質量,盡量縮短內容到交易的距離,就是他們目前在做的事。 「旅游本身就是閑賦經濟,不是生活必須品,讓大家閑著沒事兒就花錢出門,這點有點本事,這背后就一定得有品牌的溢價」。 韓哲覺得品牌的東西一定要好的內容觸達人們的心靈,「IP產物的打造可探索的方式很多,但核心還是離不開發現用戶的消費需求。」但與阿里旅行的大而全不同,窮游的策略依舊謹慎。 「直播,VR我們肯定是高度關注,也有一些嘗試,我們還是比較有耐心的在觀察,然后看看我們可以做些什么,可能有些東西注定就是離窮游遠的。」 說起現在,韓哲自己也有感慨,「今天的環境噪音太大了,各種玩的東西太多了,用戶的屁股坐不住,社區得沉的下來。」 其實窮游與螞蜂窩本身就是一個大IP,而窮游更是一直在嘗試IP的開發。韓哲說,他們不但對PGC的窮游錦囊是新版,往個性化錦囊的方向嘗試;今年還發布了生活美學的大IP產品——JNE。 「其實用戶在消費的是這個美感物件背后的文化故事,一個身份認同,欣賞的是傳統匠人的堅持和手藝。」韓哲透露,窮游為了原創視頻內容的開發,還專門建立了一個小的視頻團隊,做了一系列的節目——窮游葩葩趴。 而螞蜂窩即具備的UGC和媒體屬性,本身又是自由行服務平臺,也成為了很多目的地、景區,甚至影視作品打造自己的IP土壤。 如今,駕著內容創業的東風,螞蜂窩、窮游所沉淀的內容價值被業界重新審視,但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由于內容生產的高成本讓單純生產旅游內容的媒體難以盈利,單純的游記類創業已是強弩之末。 韓哲自己覺得,現在單純做游記的機會不大了,「一方面是智能工具越來越完善,傳統游記的價值在降低,另一方面旅游這種閑賦經濟一定得做成IP才能贏利,光靠游記一種工具做IP有點單薄了,得多種武器齊上陣。」 人們總擔心情懷會在與商業的碰撞中完敗,從2011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創業大潮已經冷卻,即便資本是個只講利益不問對錯的究極體,「IP」、「內容」讓創業者們也有了喘息之機。 眼瞅著窮游與螞蜂窩的商業化道路越走越寬,離最初的旅行社區越來越遠,雖然有一些簇擁略感失落,但畢竟也是站著就把錢賺了。先保證活下去,讓情懷落地,終究不是一件壞事。 |